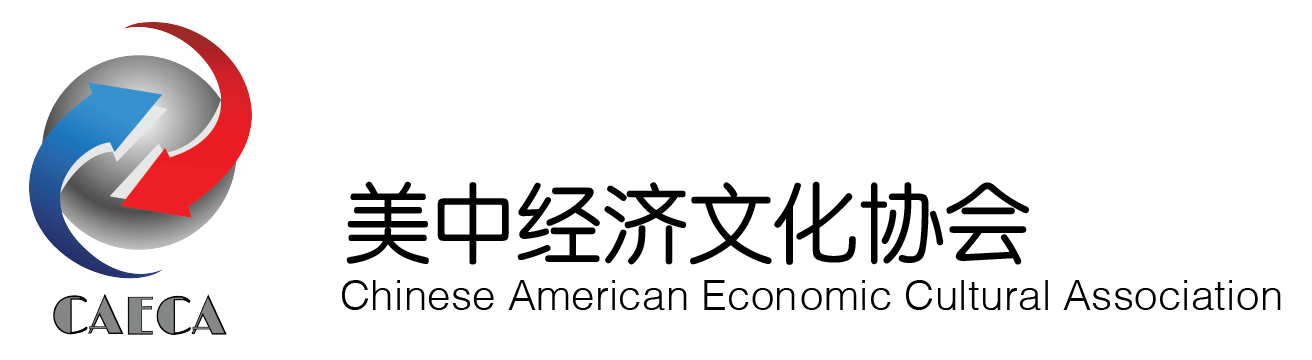2025年9月19日 美中经济和文化协会一行拜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先生
会议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
会议地点:北京大学
参会人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 林毅夫
美中经济和文化协会创始主席、著名侨领卫高荣先生
美中经济和文化协会主席牛志文
美中经济和文化协会副秘书长李书平
美中经济和文化协会董事 李增祥、谭瑞明、陆建、张伟用
美中经济和文化协会顾问卫佩琳、张珺及其他成员
记录:姚炜娇
摘要:
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与美中经济文化协会代表团座进行深入座谈。他从以两大核心板块展开:一是,对内系统回应“日本覆辙论”、“国进民退论”等国内核心焦虑,凝聚发展共识;二是,对外深刻剖析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论证中国凭借独特优势必将胜出的逻辑。本次林毅夫院长的分享中,不仅以经济学阐述现况,更是在关键节点中对中国战略信心的宣誓,为理解中国经济现状与未来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会议背景和核心议题界定
时代背景的特殊性
本次座谈会发生于一个极其复杂且关键的宏观窗口期:
全球层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陷入长期性停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构。
中美关系层面:自2018年贸易战开启,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已延伸至科技、金融、地缘政治等全方位领域。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已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外部变量。
中国国内层面: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转型攻坚期,正经历经济结构升级带来的阵痛,包括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地方债务化解、以及社会舆论对民营经济活力、青年就业等问题的高度关注。
与会方代表性
美中经济文化协会:其成员多为穿梭于中美之间的企业家、投资者与学者,他们对两国政策环境、市场情绪有切身感受,其带来的问题(如企业出海、出口下滑、民企困境)极具现实性和代表性,反映了市场一线的真实关切。
林毅夫教授: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创立者,其理论体系强调发展中国应基于自身“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他本人参与中国高层经济决策咨询,其观点被视为解读中国政策方向的重要风向标。
核心议题
基于以上背景,座谈会自然聚焦于以下几个牵动全球神经的核心议题:
中国与日本,是否都在被美国打压后陷入长期经济停滞?
如何看待当前民营经济困难与国有企业投资增加现象?
产业政策究竟是“制胜法宝”还是“资源错配”?
在中美长期竞争中,中国的长期产业发展战略?
对内回应——廓清迷雾,构建发展共识
林毅夫教授对国内关切的回应,基于其经济学比较分析和逻辑推演。
对“日本参照系”的不同看法:发展阶段与政策选择的辨析
强调发展阶段与增长潜力的差异。
林毅夫指出,衡量经济发展阶段需关注人均GDP水平。他认为,日本在1990年时人均GDP已达到美国的130%,处于全球技术前沿,增长模式需转向创新驱动,难度增大。而在他看来,中国当前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至1/6,这意味着中国仍拥有通过技术模仿、消化吸收实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其增长潜力和空间与当年的日本不同。
强调产业政策选择的不同影响
林毅夫认为,日本经济停滞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在达到顶峰后受国内外思潮影响,基本放弃了积极主动的产业政策,导致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未能占据领先地位。而他指出,中国则持续运用产业政策(如《中国制造2025》)支持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并认为这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成效。
结论
在林毅夫的分析框架下,中国与日本在1990年代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政策选择,因此他不认为中国会重复日本的道路。
对“国进民退”现象的解读:全球总需求视角下的分析
对于民营经济困难与政府投资增加并存的现象,林毅夫提供了他的分析视角。
溯源本质:外部需求变化是主因
林毅夫指出外部需求变化是主因。他引用数据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OECD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外需环境面临挑战。
传导机制:民营企业承受外部冲击
民营企业承受外部冲击。林毅夫强调了一个数据:中国大量出口由民营企业贡献。因此,全球外需变化直接影响出口导向型民营企业,导致其订单减少、投资意愿低迷,表现为经营困难,在数据上显现为民营部门活力的“相对收缩”。
政府行为:逆周期调节以稳定经济
逆周期调节以稳定经济。林毅夫认为,在此背景下,政府出于“稳就业、稳增长”的职责,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来托底需求。而这些项目多由国有企业承建。因此,在他看来,表面上看到的“国进”,是政府为应对民营部门因外部冲击而“民退”所采取的逆周期调节措施的结果,而非国有部门主动扩张、挤压民营空间的原因。
共生关系:政府投资最终惠及民营企业
林毅夫进一步指出,政府的这些大型投资,其所需的大量原材料、设备、技术服务等向民营企业采购。因此,他认为政府的投资实质上是在为处于困境中的民营企业创造订单、维系生存。他视二者为“同舟共济”的共生关系。
对外剖析——中美战略竞争的视角
林毅夫教授对中美竞争的分析,阐述了他视角下的中国优势。
对美国战略的评估:质疑其有效性
林毅夫对美国当前对华采取的某些策略,尤其是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新的视角。
对美国产业回流政策的思考
他认为,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旨在吸引或逼迫企业在美国本土生产诸如服装、家电等产品。这些产业是美国基于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早已转移的、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强行推动这些产业回流,在他看来可能造成经济资源的低效配置,其政策有效性面临挑战。
对加征关税的思考
以对华加征高关税为例,林毅夫分析了其可能的影响。他认为美国无法自己生产大部分消费品,高关税并未减少需求,只是改变了供应渠道:从直接由中国进口,转为从越南、墨西哥等国间接进口。而这些国家的产业链不完整,其中间品和核心部件仍需从中国采购。这可能导致:
美国进口成本上升;
中国对美直接出口额下降,但对东南亚国家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实际总影响可能小于表面数据。因此,他认为美国的行为可能效果不彰。
对美元政策的思考
林毅夫对美国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可能对美元的国际信用带来长期风险。
论证中国优势:阐述其视角下的三大竞争力
林毅夫认为,中国在中长期竞争中拥有一些显著的优势。
人才规模优势(The Talent Base):他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人才。中国每年这方面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巨大。这被认为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人才库,有利于研发和创新。
市场规模优势(The Market Scale):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之一。这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能在中国快速达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有助于摊薄成本。同时,巨大的市场也可能带来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
产业生态优势(The Industrial Ecosystem):
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大类的国家。这种完善的工业体系意味着较强的供应链效率和创新转化能力。任何创新想法都能在中国找到快速实现的路径。
林毅夫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作为例证:在美国发展面临产能瓶颈,而在中国迅速实现大规模量产。这被视为中国全产业链配套优势的体现。
问答与互动——聚焦实操与理论争议
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美国
林毅夫持谨慎态度。他预判了可能面临的高劳动力成本、工会文化等结构性障碍。他认为,追随美国政治口号而非市场规律前往投资,风险较高,并以富士康此前在美建厂计划遇阻为例证。
关于产业政策争议与“统一大市场”
针对国内学界对产业政策的质疑,林毅夫承认许多产业政策失败了,但他认为关键在于“不能因噎废食”。他的核心论点是:产业政策是追赶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 他认为最新提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有助于优化产业政策环境。它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迫使各地更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制定产业政策,从而可能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注: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是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的重要争议,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是其中一派代表。本会议纪要客观呈现了林毅夫教授在座谈会上的主要观点。他的论述旨在阐释其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信心来源,其信心基于对中日差异的分析、对国内经济现象的解读以及其视角下的中国竞争优势。